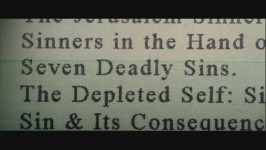大島渚的【少年】--- 是嚴謹有度? 還是小題大做?
前言
大島渚早期至中期的作品 (我視【夏之妹】為導演中期最後一套作品),在內容上大部份一向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,對現存日本的政治、社會及傳統家庭關係極度不滿,反映出它們的問題及缺點,技巧手法則非常眩目,無論外向 (例如【日本之夜與霧】 、 【白晝的色魔】 ),抑或內歛 (例如【儀式】 ),都給人一種很強烈的視覺風格。而1969年的【少年】 ,則一反常態,內容簡單,技法傳統,無論國內或國際上,也具有很高的評價。
故事梗概
故事講述在日本有一家四口,包括十歲的少年 (阿部哲夫飾),曾在戰爭中受傷的父親 (渡邊文雄飾),少年的繼母 (小山明子飾),以及年僅三歲同父異母的小弟弟 (木下剛志飾),不斷過著流浪的日子,而謀生的方法,就是去欺騙和敲詐別人。母親往往假裝被汽車撞倒,而父親則連忙趕上去恐嚇那些無辜的駕駛人,勸誘他們免於被控上法庭而先給予賠償。大多數的駕駛人都害怕麻煩而墮入了他們的圈套,雙方講數後賠款了事。
其後,有一回父母在雪地上爭吵,小弟弟在眾人疏忽下走出車路,迎面而來的一輛汽車為了閃避他而撞上電柱,司機當場喪生,鄰坐的少女也犠牲。自始以後,父親決定放棄犯罪生涯,但這時警察卻追蹤而至,把他們拘捕歸案。少年被帶往問話時,起初默言不語,但當他記起那死去少女的容顏時,淚水便忍不住奪眶而出,承認到過北海道犯罪。 (以上兩段節錄及修改自舒明著的 <<日本電影風貌>>,頁308-310)
內容的安排
影片是取材自一件真實的事件 (像【白晝的色魔】及【感官世界】 ),然後導演及編劇再稍加修改及潤飾,注入他們的世界觀及意義在電影內。而很明顯的, 【少年】的重心,是放在描寫1) 少年的孤寂;2) 他對家庭忍受的愛;3) 以及渴望衝出固有的障礙而建立自己的一套人生思想。在內容上,可以看出,導演很有心思地安排每個情節、每個人物動作,去develop那些重心,甚至技巧每每配合得宜。比方說,少年在沙灘上的一場戲,便以四週無人加上人工打燈,來突顯少年的孤寂;在旅館內吃飯看表演,構圖則以中間一條柱來畫分少年與家人,暗示其格格不入的割裂關係;而少年有幾場戲在街上行走,也顯得很渺小,然後很多學生在他身邊擦過等等。男主角雖百般不願意,但為了家庭 (尤其是媽媽),也幹非法勾當。加上幻想自己是宇宙人,冀望自己不再是現在的自己。
以上的東西雖每每「對號入坐」,但筆者未能感受到那份悲戚感,而這份感情,對影片來說其實是很重要的。原因之一, 【少年】是建基於一個寫實的架構之上,而以影片的題材來說,寫人寫情,直達少年的內心世界,以令觀眾動容,這個要求我認為是合理的。偏偏大島渚卻以冷冷的旁觀者角度切入,在一些necessary的地方又做不到動人的效果。例如少年在沙灘上的一場戲,便喊得很「行貨」;北海道的戲份,雖有環境渲染,但少年太「木口木面」 (我想這不是「非職業演員」的問題,而是導演處理的問題),鏡頭捕捉他的情緒不夠,所以打爆雪人/宇宙人一場感染力不足。我不知大島渚是否故意這樣做,但,以這麼一個題材來說,適當地運用傳統通俗劇的元素或方法,來動之以情,我認為是應該的。
真幻交錯
而【少年】在寫實的架構上,又混合了幻象的元素在內,這方面的結合,倒是頗成功的。例如少女撞車死亡的一場戲,暗藍的單色畫面、時而切掉的音效、醫護人員「看不見」少年等,混合在一起,的確有真幻交錯的效果。加上林光的配樂,更加強這種曖昧的味道及氣氛。大島渚在游走於寫實/真實與幻象之間,放棄了 (或是根本做不到) 溫暖的動人情感,以遷就冷冷的曖昧感覺,是為影片美中不足之處。
小題大做?
【少年】另一令筆者失望之處,是導演硬要把他一向對日本的政治及建制不滿狀況,投射於影片之中,在電影的肌理上,不但不能承受它們被放於影片內,而且格格不入,破壞了男主角內心深處的心理描寫。最明顯的一段,莫過於片首的字幕,日本軍國國旗,及黑色圓心,來暗示日本政治建制哀歌的隱喻,呼之慾出。情節上,渡邊文雄飾演的父親,則曾向少年說一些戰爭的傷痕,再加上配樂的悲哀情調,大島渚的意圖可謂不言而喻。這些東西,筆者認為在【儀式】內是恰如其份,但放在【少年】內,其故事真的能夠支撐到這麼大的一個theme嗎? 對筆者來說,未免有小題大做之嫌。